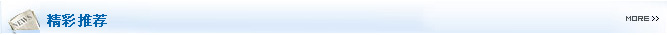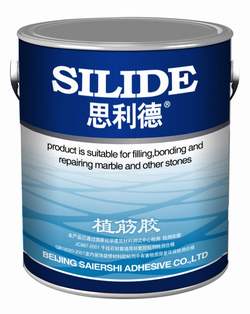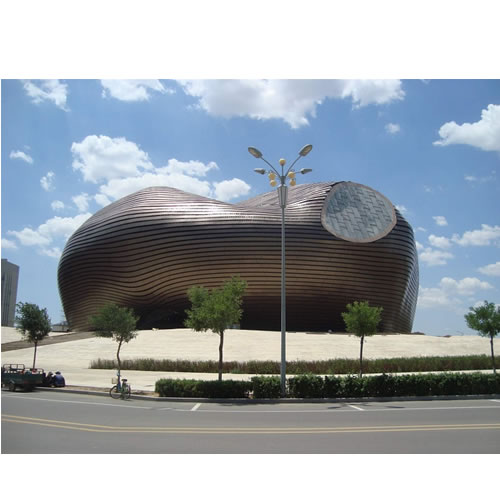然而,這一市場(chǎng)的風(fēng)向轉(zhuǎn)機(jī),并沒有被中國的3D打印企業(yè)準(zhǔn)確把握。多數(shù)院校體系的企業(yè)仍專注于工業(yè)設(shè)計(jì)領(lǐng)域。而“三校一企”中的企業(yè)——北京隆源自動(dòng)成型系統(tǒng)有限公司則致力于為軍工和少量發(fā)動(dòng)機(jī)領(lǐng)域提供服務(wù)。
具有清華大學(xué)背景的北京太爾時(shí)代科技有限公司(下稱太爾時(shí)代)是調(diào)整了產(chǎn)品技術(shù)方向的極少數(shù)企業(yè),“通過與市場(chǎng)接觸,發(fā)現(xiàn)小型設(shè)備在當(dāng)前更具有市場(chǎng)推力”。其副總經(jīng)理顏旭濤介紹,
2011年,太爾時(shí)代售出小型機(jī)3000多臺(tái),2012年增長更快。
而在江浙一帶勇于嘗試新鮮事物的企業(yè),大多數(shù)屬于并不具備研發(fā)實(shí)力的中小企業(yè)。它們能做的,不過是購置幾臺(tái)工業(yè)級(jí)3D打印機(jī),像提供復(fù)印服務(wù)的便利店一樣,為客戶提供打樣等服務(wù)。也有一些有野心的企業(yè)會(huì)從國外進(jìn)口核心部件,做幾款樣機(jī),或者模仿進(jìn)口的3D樣機(jī)做逆向研發(fā)。
小型3D打印機(jī)已激增為一塊“看得見的”市場(chǎng),同時(shí),也帶動(dòng)工業(yè)級(jí)3D打印機(jī)市場(chǎng)逐漸有了起色。快速制造領(lǐng)域國際權(quán)威報(bào)告《沃勒斯報(bào)告2012》顯示,截至2011年,全球累計(jì)銷售4.9萬臺(tái)工業(yè)級(jí)3D打印機(jī),其中近四分之三由美國制造,以色列和歐洲各國的份額分別為9.3%和10.2%,中國生產(chǎn)的設(shè)備僅占3.6%,與日本相當(dāng)。而全球領(lǐng)先的六家3D打印設(shè)備制造公司,2008年銷售收入達(dá)6.96億美元,占行業(yè)總收入近60%。
此時(shí),歐美充滿活力的3D打印企業(yè),不僅在技術(shù)上嘗新,而且在商業(yè)模式上也有創(chuàng)意。
2007年由飛利浦提供啟動(dòng)資金的Shapeways,令人矚目的就是它“云打印”概念的O-O(線上線下)商業(yè)模式。它像Facebook一樣打造自己的用戶社區(qū),社區(qū)集銷售、定制、設(shè)計(jì)于一體:顧客可以在網(wǎng)上選定產(chǎn)品的三維設(shè)計(jì)方案,或直接上傳自己設(shè)計(jì)好的3D模型,并選擇材料,支付一定費(fèi)用后,Shapeways會(huì)用3D打印機(jī)將其制造出來并郵寄上門。截至2012年6月,該公司累計(jì)打印超過100萬件產(chǎn)品;其制造社區(qū)中有超過6000家提供設(shè)計(jì)服務(wù)的商家和個(gè)人;還有15萬活躍用戶。
Shapeways以技術(shù)和新的商業(yè)模式先后贏得三輪融資,總金額超過1700萬美元,由此實(shí)現(xiàn)了其在紐約創(chuàng)辦“未來工廠”的夢(mèng)想。
由于3D打印在美國制造業(yè)的巨大應(yīng)用潛力清晰顯現(xiàn),美國總統(tǒng)奧巴馬2011年宣布,并在2012年國情咨文中重申:政府計(jì)劃每年向先進(jìn)制造技術(shù)投資5億美元,并在四年后,提高到每年10億美元,以提升美國的領(lǐng)先地位。
中國的科研、工業(yè)界也開始重新審視思考這一技術(shù)。2012年,顏永年重返3D打印領(lǐng)域,他發(fā)現(xiàn)最大的變化是:“以前需要跟政府官員講解半天什么是3D打印,現(xiàn)在省了不少口舌。”
共性技術(shù)缺失:產(chǎn)研學(xué)錯(cuò)位
太爾時(shí)代,是2003年顏永年和幾個(gè)學(xué)生湊錢成立的。限于清華教授的身份,顏當(dāng)時(shí)未直接參與運(yùn)營,其子顏旭濤是公司副總經(jīng)理。
在攻克小型3D打印FDM設(shè)備時(shí),太爾時(shí)代遇到了如何能讓噴頭順暢、穩(wěn)定地出絲,如何提高精度,如何增加可打印材料的多樣性等問題;而工業(yè)級(jí)3D打印機(jī)的研制中難啃的骨頭更多:材料、微滴噴射技術(shù)和激光技術(shù)等,這些被業(yè)內(nèi)人士稱為“共性技術(shù)”。
事實(shí)上,不僅是3D打印企業(yè),中國目前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碰到的核心瓶頸,就源于產(chǎn)業(yè)共性技術(shù)的嚴(yán)重缺失。
所謂共性技術(shù)是指那些蘊(yùn)含潛在機(jī)會(huì)——可以在多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中廣泛應(yīng)用——的技術(shù)或工藝,它既是基礎(chǔ)研究邁向市場(chǎng)應(yīng)用的第一步,又具有被一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或多個(gè)產(chǎn)業(yè)共享的潛力。可見,共性技術(shù)的突破,與基礎(chǔ)研究和應(yīng)用研究皆密不可分。
在發(fā)達(dá)國家的創(chuàng)新體系中,大學(xué)主要進(jìn)行基礎(chǔ)研究,研究所側(cè)重于共性技術(shù)研究,企業(yè)主要致力于應(yīng)用性研究和最后的產(chǎn)品化,產(chǎn)研學(xué)三方在市場(chǎng)機(jī)制下合作互補(bǔ)。但在中國,這三者的關(guān)系,卻呈現(xiàn)出錯(cuò)位競(jìng)爭(zhēng)的局面,致使科研與產(chǎn)業(yè)嚴(yán)重脫節(jié)。
從大學(xué)來講,對(duì)基礎(chǔ)研究的熱情正在下降。基礎(chǔ)研究,是原始創(chuàng)新的基礎(chǔ),它意味著人才的培養(yǎng)、數(shù)據(jù)和成果的積累。中國科學(xué)技術(shù)發(fā)展戰(zhàn)略研究院常務(wù)副院長王元稱,基礎(chǔ)研究和前沿技術(shù)的布局,關(guān)系一個(gè)國家十年二十年的發(fā)展,因此穩(wěn)定持續(xù)的投入非常重要。
然而,1999年后,中國的基礎(chǔ)研究占研究與試驗(yàn)發(fā)展經(jīng)費(fèi)(R&D)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(shì)。2005年至2010年,這一比例從5.36%降至4.59%,而美國基礎(chǔ)研究經(jīng)費(fèi)始終占R&D總支出10%以上,經(jīng)濟(jì)合作與發(fā)展組織成員國中,法國、澳大利亞、瑞士均在20%以上。
與此同時(shí),中國的大學(xué)越來越熱衷于應(yīng)用研究,且伸長手腳,自辦企業(yè)。3D打印產(chǎn)業(yè)就呈現(xiàn)出濃厚的“高校軍團(tuán)”的色彩:除清華大學(xué)的北京殷華外,西安交通大學(xué)派生出陜西恒通智能機(jī)器有限公司,武漢濱湖機(jī)電技術(shù)產(chǎn)業(yè)有限公司則依托于華中科技大學(xué)。
顏永年作為校方代表曾出任北京殷華的董事長,公司團(tuán)隊(duì)主要由他實(shí)驗(yàn)室的教師和學(xué)生及外聘的幾名工人組成。公司一年賣兩三臺(tái)3D打印設(shè)備就可以支撐運(yùn)營經(jīng)費(fèi),盈利部分則需給校方分成。很快,這個(gè)校屬企業(yè)就遇到了維持易、做大難的局面。由于經(jīng)營業(yè)績與個(gè)人收入的關(guān)系不大,且教師和學(xué)生對(duì)發(fā)表論文、評(píng)職稱的興趣遠(yuǎn)超過銷售產(chǎn)品,導(dǎo)致研究方向多瞄準(zhǔn)高、精、尖題材,對(duì)來自市場(chǎng)的信號(hào)則表現(xiàn)遲鈍。
事實(shí)上,幾家依托高校建立的3D打印企業(yè),都未能在熱銷的3D打印小型設(shè)備上有所建樹。
中國科學(xué)院原副院長楊柏齡就指出,教授抓一幫學(xué)生,辦一個(gè)小企業(yè)。這樣的產(chǎn)業(yè)化不僅對(duì)創(chuàng)建研究型高校和研究機(jī)構(gòu)不利,而且從企業(yè)規(guī)模上講,對(duì)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的貢獻(xiàn)也上不了臺(tái)面。實(shí)際上,它是滿足小團(tuán)體利益的小富即安的模式。
大學(xué)應(yīng)在技術(shù)出了“孵化期”后,將其轉(zhuǎn)給企業(yè)實(shí)現(xiàn)商業(yè)化,從而脫離高校管理。最早做出3DP打印技術(shù)的麻省理工學(xué)院,就通過技術(shù)轉(zhuǎn)讓實(shí)現(xiàn)了商業(yè)化,它把工藝分成四條技術(shù)路線,分別賣給四家公司,其中一家名為Z Corp的公司,現(xiàn)在已占據(jù)了業(yè)內(nèi)領(lǐng)先地位。
2012年,顏永年吸取往年的經(jīng)驗(yàn),徹底離開了大學(xué),他找到投資方,注冊(cè)了一家新公司。
從科研院所來講,同樣缺乏研究并解決共性技術(shù)的興趣。3D打印初進(jìn)入中國那幾年,即1999年之前,中國的科研體系還屬于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體制:企業(yè)只管生產(chǎn),技術(shù)研發(fā)由科研院所進(jìn)行,并無償轉(zhuǎn)讓給企業(yè),結(jié)果前者沒動(dòng)力,后者研發(fā)能力薄弱。是年7月,國務(wù)院下達(dá)《關(guān)于加強(qiáng)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,發(fā)展高科技,實(shí)現(xiàn)產(chǎn)業(yè)化的決定》,由此啟動(dòng)科技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。
當(dāng)時(shí),全國范圍內(nèi)的上千家技術(shù)開發(fā)類科研院所進(jìn)行了轉(zhuǎn)制:脫下事業(yè)單位的“官衣”,不再享有國家財(cái)政撥款,轉(zhuǎn)變?yōu)樽载?fù)盈虧的科技型企業(yè)。
 上一頁12345下一頁
上一頁12345下一頁